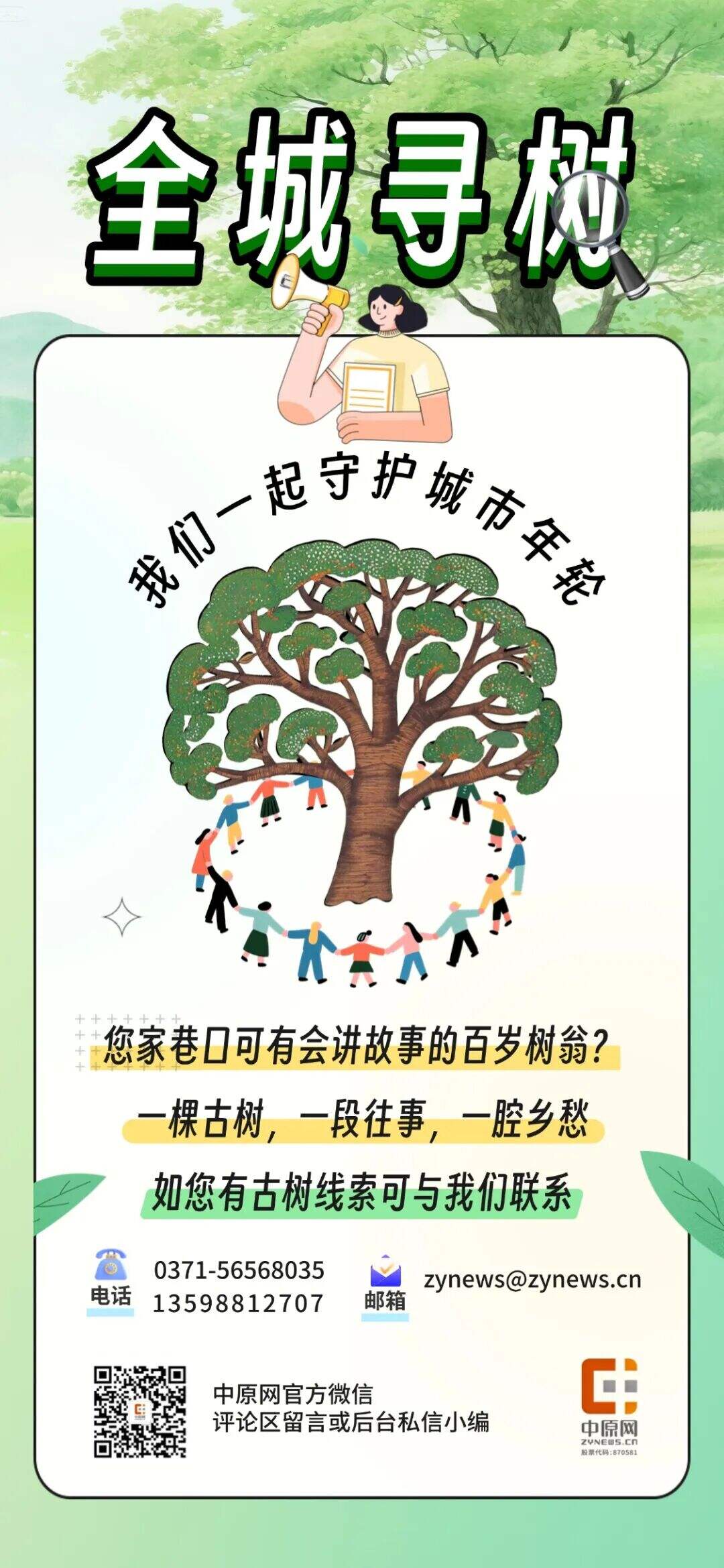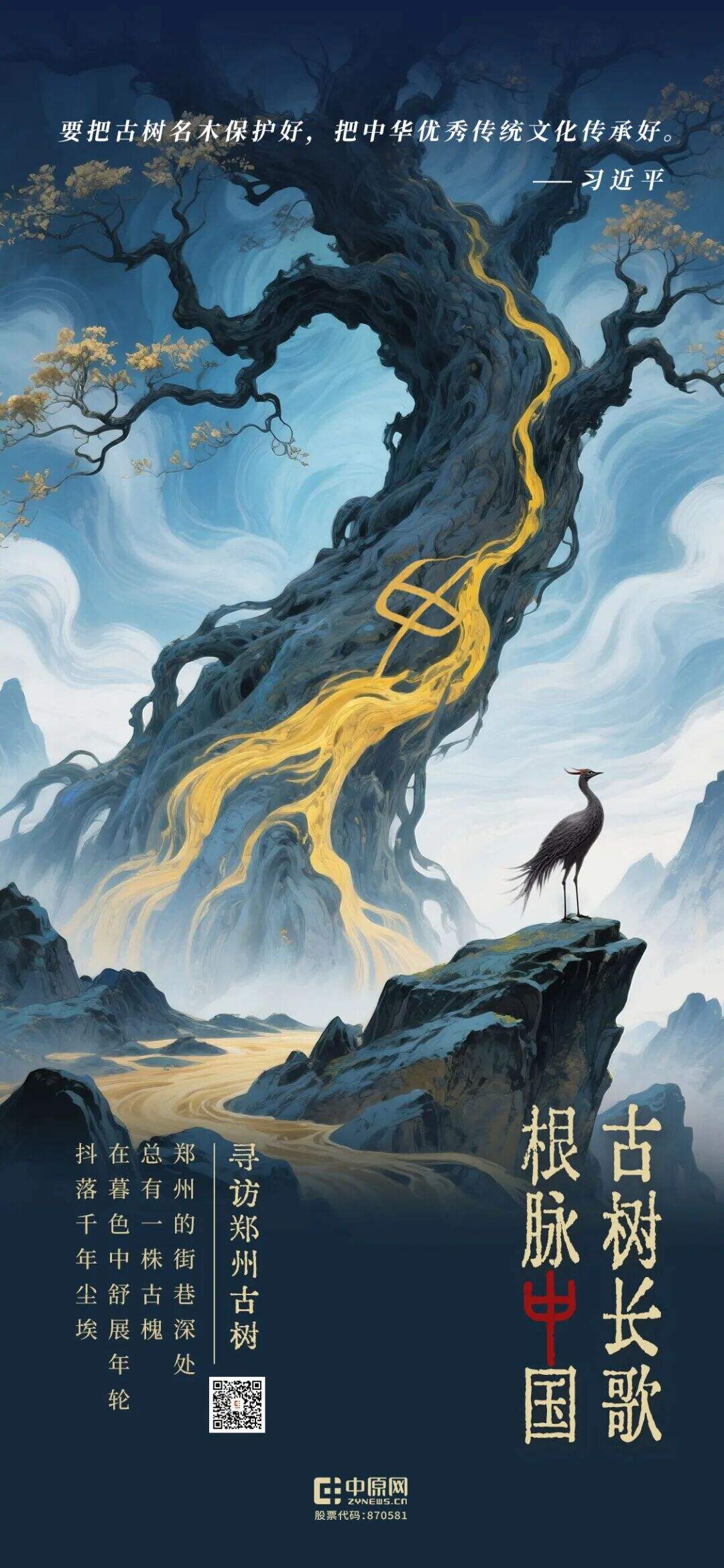
“這里就是當年祖師廟的位置,從四棵古樹中間走過去,就抵達廟址了。”七旬老人時永福站在廣場上,雙手比畫著向我們還原記憶中的原貌。他的聲音溫和細緩,作為《鄭州上街區夏侯村時氏文化志》的主筆,他對這里的歷史如數家珍。
雨后的古柏更顯蒼翠,深褐色的樹皮因濕潤而泛著光澤。老人走近輕撫著其中一棵古樹:“有時候很神奇,在這樹下散步,仿佛能穿越時空,感知到明朝嘉靖年間,我的祖輩時源左都督在此養病的情景。”
在時永福身后,四棵側柏站得方方正正,間距不差分毫,它們的前方正是夏侯村祖師廟舊址。這長在上街區金華路中段的古柏,打明嘉靖年就扎在這片土地上了,算到如今已有455歲,被列為鄭州市二級保護古樹。

△如方陣一般站列的古樹
四棵古柏站成個方方正正的陣,像支不動的儀仗隊。西邊那棵的皮最糙,鼓出的紋路像老將軍暴起的青筋;東邊那棵卻溫和,樹皮疊著云片似的,雨珠掛在縫里。它們比夏侯村后來的許多故事都早。
“原先這廟叫始祖廟,咱都喊東大廟。” 時永福的長輩曾告訴他,始祖廟也叫祖師廟,位于夏侯村東頭,也稱東大廟。相傳,這座廟建于明朝后期,歷經多次擴建,到清朝中期,廟宇已有相當規模,僅建筑群占地就有約2000平方米。整體為灰磚灰瓦建筑,雄偉壯觀。
曾經香火鼎盛,廟里的大鐘上刻滿了捐資鑄鐘的夏侯族人姓名。1954年,廟宇被拆,但四棵柏樹卻保存了下來。

△參天古柏
“小時候,這里是全村最熱鬧的地方。”時永福說,夏天人們在樹下乘涼聊天,孩子們圍著樹追逐嬉戲,過年過節時村民會在樹下祈福。那些日子,就像發生在昨天。

△系著紅綢帶的古樹
時永福最愛蹲在樹下給孫輩講故事,話題總繞不開一個謎:“咱村叫夏侯村,可滿村沒一個姓夏侯的,你說怪不怪?”
“老輩人說,這里是夏侯惇安置傷兵的地方。”時永福說起村里的傳說——三國時期,夏侯惇兄弟在此與敵軍交戰,傷員被安置在村東南的一條溝中養傷。后來輕傷員歸隊,重傷員痊愈后無法歸隊,便在此娶妻生子、定居下來。因為是夏侯惇的部下或后裔,故將這里命名為夏侯村。

△古樹發新芽
也有說法認為與秦末劉邦的大將夏侯嬰有關。“不管是哪種說法,都說明咱們村歷史久遠。”時永福笑著說,這些傳說就像古柏的根系,深扎在每個村民的心中。
村里姓時的占了六成,時永福的祖輩時源,明朝時還是左都督,據說就曾在祖師廟旁養過病。“說不定他也在這樹下散過步呢。”時永福笑著說。

△古樹名木保護牌
2012年,夏侯村拆遷的消息傳來,時永福和村民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這四棵古柏。
“存在的時候不覺得,失去的時候倍感惋惜,古樹一旦被損壞,就真的再也彌補不回來了。”時永福說,村民們像保護親人一樣守護著古柏,再三向開發商提出必須保護好這些古樹。
令人欣慰的是,開發商特意在古樹四周挖出透氣孔,上面鋪上木板,為古柏留出了充足的生長空間。今年春天,時永福欣喜地發現,古柏的葉子比以往更綠更茂盛了。

△古樹透氣
“村子拆遷了,但根還在。”時永福說,每逢傳統節日,總會有村民回到古柏下,聊聊家常。年輕人外出打工,回家第一件事就是來看看古柏;誰家有了喜事,也會到樹下報個喜。
“我們這個村子,年輕人幾乎都出去了,就剩下我們這些老人家守著。”我們明白,這四棵古柏也是他心里的“老人家”,陪著夏侯村人走過一輩又一輩。

△古樹周圍景象
如今的四棵古柏,站在商業廣場中間,倒比從前更熱鬧了。
下午4點多,陸續有居民來到古柏下。老人們下棋聊天,孩子們玩耍嬉戲,年輕的媽媽推著嬰兒車在樹下散步。四棵古柏靜靜佇立,見證著新時代的煙火氣息。
“現在天天能見到它們,真好。”時永福說,只要古柏在,夏侯村就永遠在。它們不只是一棵樹,更是一座村莊的記憶,一代代人的鄉愁。

△古樹如高樓
夜幕漸漸降臨,廣場上的燈一盞盞亮起。時永福慢慢走回對面的新家。
他回頭最后望了一眼古柏。在雨幕和燈光的交織下,四棵古柏的輪廓顯得格外深邃。
新的一天,這位七旬老人還會準時出現在古柏下。而古柏,依舊以它們的方式守護著這里——見證著孩童長成少年,見證著新鄰變成故交,見證著尋常日子里的每一個溫暖瞬間。
這就是生活最樸素的真相:有些守望,注定要穿越更長的時光;有些根脈,早已在變遷中生生不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