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
日軍侵入滄州城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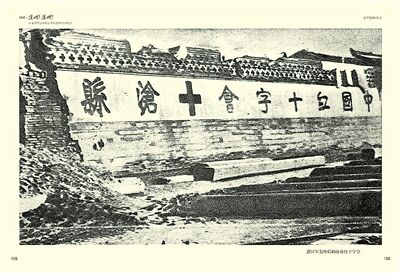
1937年9月29日,日軍侵入獻縣城
清晨,陽光穿過薄云,將滄縣捷地炮樓包裹在一片滄桑凝重之中。這座始建于1937年的日軍據點,像一道傷疤,深深地烙印在滄州大地上,見證著那段血與火的歲月。
1937年9月,侵華日軍沿津浦鐵路南下,9月24日,滄州淪陷。此后,日軍在這里進行了長達8年的殺戮和掠奪,制造的慘案數不勝數——在青縣流河鎮,僅半天日軍就屠殺了186人;在滄縣張辛莊,138名村民慘遭屠殺;在泊頭市軍屯村,143名百姓遇害……樁樁件件,罄竹難書。
硝煙雖已遠去,但歷史不容忘記。有些記憶,終將化作前行的力量。
滄州日報全媒體記者 楊靜然
一城之殤 戰爭傷痕無法磨滅
1937年7月7日深夜,盧溝橋的槍聲劃破夜空。
日本侵略軍蓄意制造“盧溝橋事變”,中華民族全面抗戰從此開始。事變發生后,日軍很快占領北平、天津,并沿平漢、津浦鐵路線迅速南犯,一路大肆燒殺搶掠。
9月9日,日軍侵入青縣流河鎮,對流河鎮小王莊村民進行了殘酷的屠殺。僅幾個小時,只有37戶、180口人的小王莊村,就被殺死了30人,燒毀房屋100多間。流河鎮不足500戶,日軍半天就屠殺了186人,炸毀、燒毀民房700多間。
此時,滄州城已經岌岌可危了。
日軍繼續南侵,遭到愛國官兵奮起抵抗。日軍以飛機和重炮輪番轟炸,而守軍沒有重火力掩護,全憑機槍、步槍、手榴彈和大刀,與日軍浴血奮戰。但敵我力量懸殊,守軍堅守數日后,滄州城(時滄縣城)被攻陷。那一天是9月24日,冀中平原秋色宜人,滄州城卻被滾滾濃煙和血腥籠罩。從此,日軍開始了長達8年的血腥統治,給滄州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。
那一年秋天,正是莊稼收獲的季節,可滄縣張辛莊村將遭受滅頂之災。在姚官屯戰斗中遭遇頑強抵抗的日軍,闖入張辛莊后,為了泄憤,殺人放火、奸淫搶掠,老弱婦孺都未能幸免。全村青壯年100余人死亡。慘案發生后,整個村莊陷入恐怖中。
9月25日,日軍在滄縣捷地遭到中國守軍阻擊,一上午未能向南進犯,于是對捷地村百姓進行報復,挨家挨戶搜查,見人就殺。僅半天時間,全村就有114名無辜村民被日軍殺害,捷地古鎮陷入腥風血雨之中,這就是著名的“捷地慘案”……
當時,日軍為了鞏固統治,在津浦鐵路沿線修建了許多炮樓據點,捷地炮樓就是其中之一。捷地村的老人們回憶,日軍為了修建這座炮樓,逼迫捷地村和附近幾個村的村民,每家必須出5塊磚以及1名勞力。在日軍刺刀的威逼下,村民們建起了這座炮樓。“炮樓共3層,兩層供當年日軍居住。炮樓建成后,日軍又在附近建了兵營,駐扎了50多個日本兵。”
為將這座日軍侵華的鐵證保存下來,當地村民一直守護著這座炮樓。
80多年過去了,捷地炮樓依然矗立在津浦鐵路旁,如同一道永不愈合的傷疤,向世人訴說著那段血與火的歷史。
鐵證無言 歷史真相不容篡改
歲月無聲,歷史有痕。
80載光陰流轉,抗戰的烽火歲月依然銘刻在中華民族的記憶深處。在滄州,有人用執著將這份記憶延續——72歲的退休干部田書生,花費20多年時間,在故紙堆里查找,輾轉各地尋覓,通過各種方式搜集日軍侵華罪證,如今已收集各種資料80余冊,其中包括200多張珍貴的照片。
“我們不需要戰爭,但我們需要了解戰爭。”田書生語氣沉重地說,“這些照片是日軍侵占滄州時,隨軍記者拍下來的,真實再現了日軍在滄州犯下的滔天罪行,成為日本侵華的有力證據。”
2015年,田書生將這些照片編輯成冊,出版了《1937·滄州!滄州!》一書。翻開書頁,80多年前塵封的一幕幕立刻呈現眼前:津浦線上一路入侵的日軍、狂轟濫炸滄州城的日軍飛機、硝煙戰火中孤獨孑立的聞遠樓、滄州城耀武揚威的日本兵……一張張照片,一幕幕場景,讓人心痛不已。
田書生不僅收藏歷史,更致力于讓歷史發聲。他把這些影像資料一張張放大,一次次在滄州展覽,引發了強烈反響。
這些照片即使只看一眼,也將永遠難忘——
一張,是日軍轟炸滄州城后引起大火,濃煙滾滾,陰霾陣陣,聞遠樓在烽火中煢煢孑立;
一張,是日軍站在城門樓,趾高氣揚地俯視著淪陷的滄州城;
一張,是路旁孤苦伶仃的女孩,赤腳單衣,眼中盡是恐懼與絕望;
…… ……
在這些觸目驚心的照片背后,還隱藏著更多不為人知的血淚故事。除了青縣流河慘案、滄縣張辛莊慘案、滄縣捷地慘案,還有1937年9月27日,日軍兵分兩路闖入南皮縣十二里口村和七里口村,見房子就燒,見人就殺,到處是村民的慘叫聲。這次慘案,兩村共被殺害93人。1939年,日軍在肅寧縣制造了付家佐慘案、大曹村慘案。在大曹村慘案中,日軍殺害百姓73人,燒毀房屋2300余間,欠下了肅寧人民累累血債;1941年9月24日、26日、28日,日軍輪番轟炸海興縣小山集市,炸死村民130多人;1943年,日軍在任丘搞的“新國民運動”長達6個月之久,共屠殺百姓500多人,致殘1000多人,制造了震驚整個冀中的大慘案……
史料顯示,從1937年到1945年,侵華日軍在滄州進行了長達8年的殺戮和掠奪,滄州直接傷亡人數近9萬人,一次死亡10人以上的慘案達47起,百人以上的慘案6起,犧牲在滄州大地上的縣團級干部達百人……
“每當夜深人靜,我重新審視這些圖片時,感受到的不僅是悲痛,更是一種沉甸甸的民族責任。”田書生坦言。
回憶不是為了咀嚼苦痛,而是為了銘記那段不能忘卻的歷史,吾輩自強。
歷史回響 苦難指引前行方向
夏日午后,68歲的溫東生站在軍屯抗戰烈士紀念園內,斑駁的陽光透過松柏枝葉,在他布滿皺紋的臉上投下細碎的光影。他走上前輕撫軍屯慘案紀念碑,仿佛又聽見父親溫希忠臨終前的呢喃:“那天……鬼子把全村人趕到大場里……”“我僥幸活了下來,但家里17口人,死了14口。”
溫東生的父親溫希忠,曾是日本侵略者1945年在泊頭軍屯村制造的“軍屯慘案”的幸存者。
1945年5月2日,因一名士兵失蹤,日軍包圍了軍屯村,以交出士兵為由脅迫村民未果,隨后展開屠殺。5月3日至8日,日軍將抓捕的200多名村民分批押至淮鎮據點及蓮花池刑場,采用砍頭、刺刀刺殺、活埋等手段殺害百姓,累計造成143人遇難,其中有58名嬰幼兒。
“日本鬼子太壞了,燒殺搶掠無惡不作。”每每提起此事,溫東生總是難掩心中的憤怒。
“父親當時只有10歲,第一天鬼子在村里搜人,第二天一大早就把村子圍了起來,然后把人們都趕到一個地方,告訴大家準備幾天把村民殺完,每次殺多少,直到找出那個日本兵為止。100多口人擠在3間屋子里,為防止大家逃跑,又換了兩個地方。隨后,日軍派人挖了3個大坑,端著刺刀押著村民往坑邊走。就在離大坑還有幾十米遠時,父親看準時機跑了出來,跑了很久很久才脫離危險。”這段父親去世前反復講述的往事,在溫東生的心里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記。
在肅寧縣豐樂堡村,戰爭同樣給人留下了無法抹去的傷痛。
“1944年8月23日,鬼子從四面包圍了俺們村,一邊進村搜索,一邊抓捕老百姓,把村民們趕到一間屋里,鎖上門放毒氣,然后又放火焚燒。這起慘案,有87位村民被殺害。”村民們說。
在滄州市新華區的一套房子里,推開門,就仿佛穿越回80多年前烽火連天的歲月。這里不是普通的住宅,而是市民李俊波利用自家房屋建起的“抗戰文物展覽館”。
今年61歲的李俊波,曾是滄州市煉油廠的一名普通職工。27年來,他跑遍大半個中國,傾盡積蓄,收集了近3000件抗戰文物,每一件都是日軍侵華的罪證。
“你看,這是當年日軍的作戰地圖。”李俊波小心翼翼地展開一份泛黃的日軍作戰地圖,上面清晰標注著當年的軍事部署。
屋里整齊陳列著上千件日軍侵華實物:銹跡斑斑的日軍戰刀、泛黃的軍用地圖、廢舊的手榴彈……最令人震撼的是一個鐵盒,盒子上寫著“防毒具補修函 昭和十二年”。
李俊波說,1939年4月,在賀龍師長指揮的齊會戰斗中,日軍公然違反國際公約,對八路軍使用了毒氣彈。多年后,當他在河間的一個村落里發現這個物件時,毫不猶豫地將它買了下來。
“這些實物不會說話,但它們比任何語言都更有力地訴說著歷史的真相。”他說。
斑駁的炮樓、泛黃的照片、銹蝕的武器,都是日軍侵華的罪證。它們默默無聲,卻能發出最震耳欲聾的警示。
80多年過去了,滄州大地上的每一處傷痕都在時刻提醒著人們:銘記苦難,方能珍視和平;以史為鑒,才能開創未來。守護這些歷史的見證,不僅是為了告慰逝去的英靈,更是為了照亮前行的道路。
本版圖片由滄州日報提供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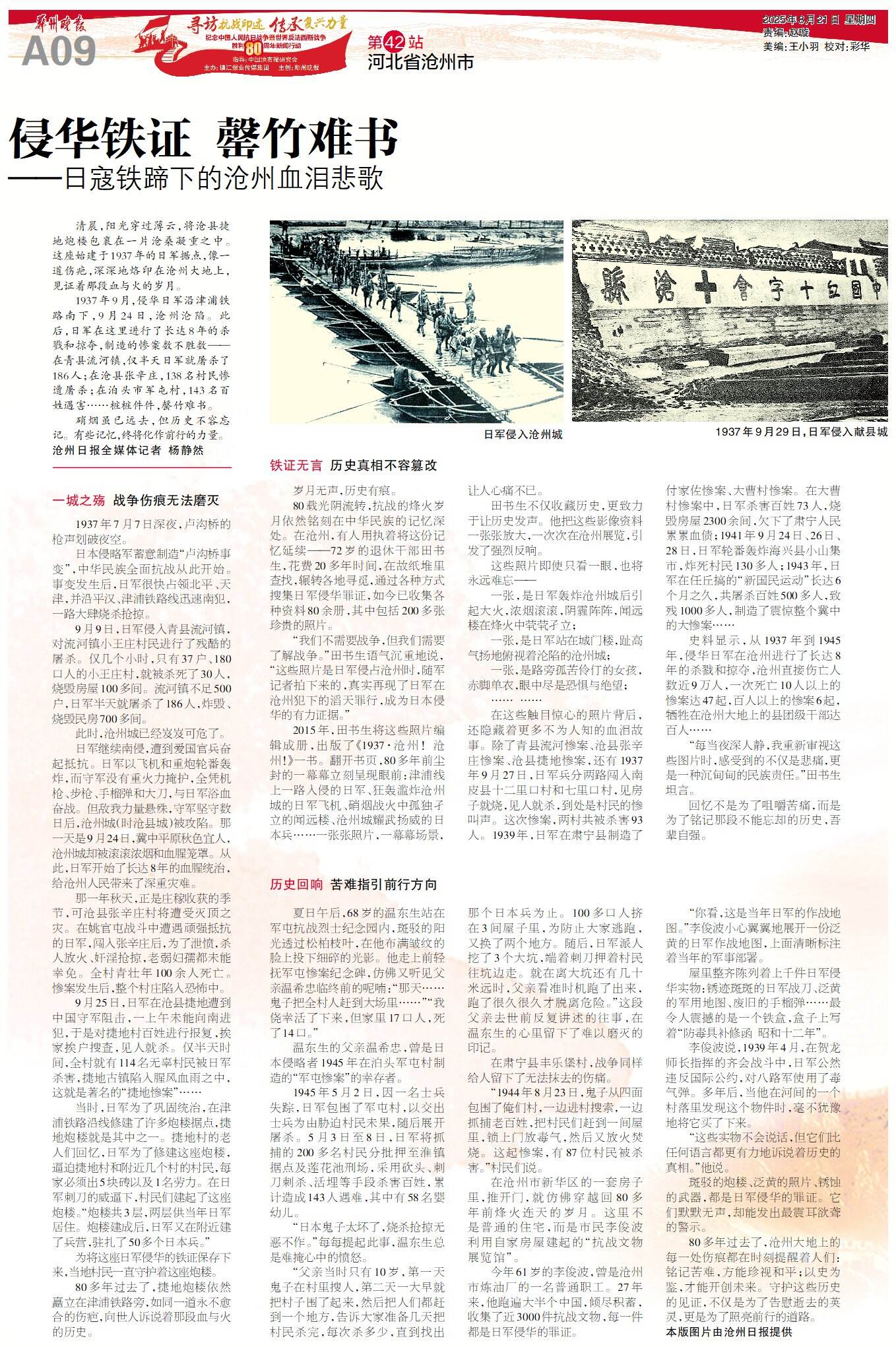
《鄭州晚報》版面截圖